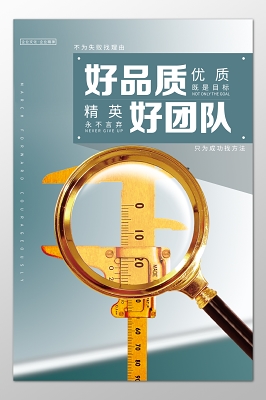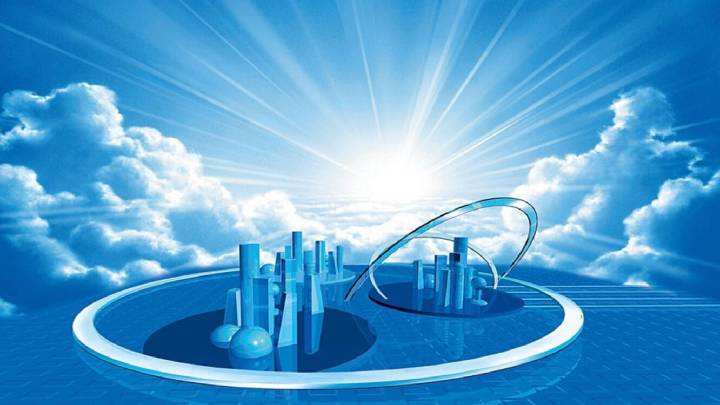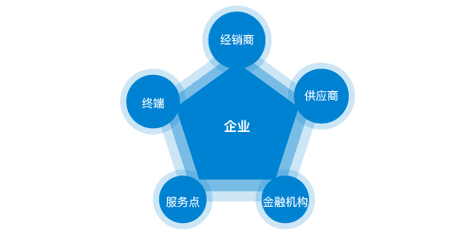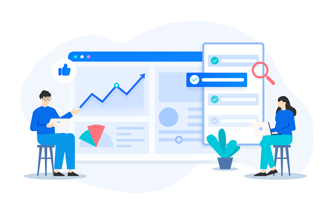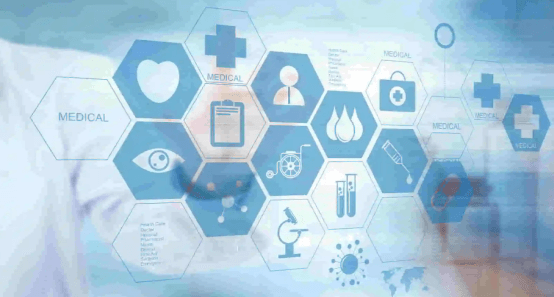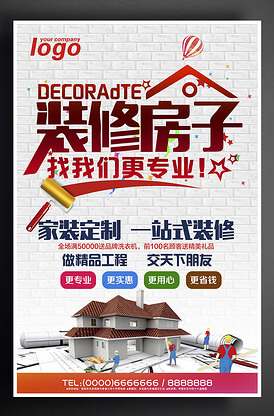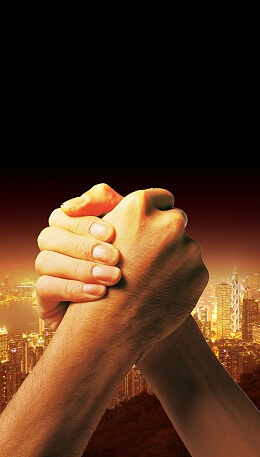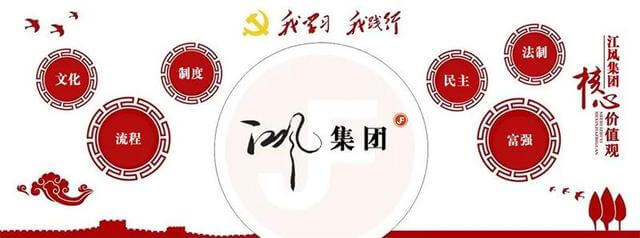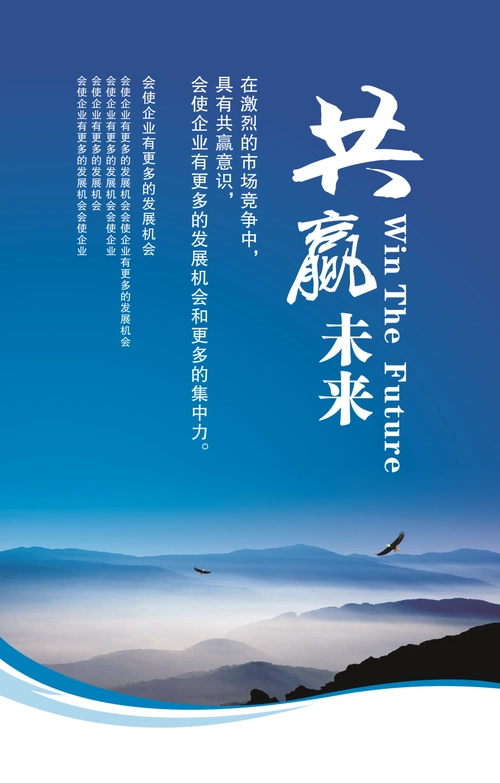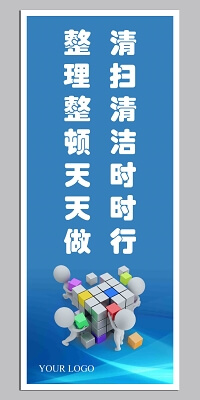叛逆青少年训练营电影-宁波若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Website Home
##规训与反叛:青少年训练营电影中的权力辩证法在《死亡诗社》的经典场景中,基廷老师让学生们撕去教科书上对诗歌的权威解读,这一叛逆举动点燃了年轻心灵的火焰。
青少年训练营题材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空间,将青春期叛逆这一普遍现象置于一个封闭的规训环境中,创造出强烈的戏剧张力!
这类电影不仅是对青少年心理的探索,更是对整个教育体系、社会权力结构的隐喻性批判。
透过这些光影叙事,我们得以窥见规训与反叛这对永恒矛盾如何在青春期这一特殊生命阶段激烈碰撞?

青少年训练营电影中的空间设置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象征。

高墙、铁门、统一制服与严格作息,这些元素共同构建出一个全景敞视的规训装置。
在《飞越疯人院》式的叙事中,训练营成为社会权力微观运作的展示场,教官代表着不可挑战的权威,而营地规则则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惩罚体系;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中精辟指出:?

权力通过空间的分配和封闭来运作,创造出一个有纪律的社会。
电影中的训练营正是这种规训空间的极端体现,它试图通过物理隔离与行为控制来?

矫正。
那些偏离常规的青少年!
然而,电影的魅力恰恰在于展现这种规训如何遭遇反叛。
从《摇滚校园》到《放牛班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如何通过音乐、艺术或小团体活动开辟自己的抵抗空间;
这些反叛行为往往始于微小的违规——一次夜谈、一首禁歌、一本私藏日记!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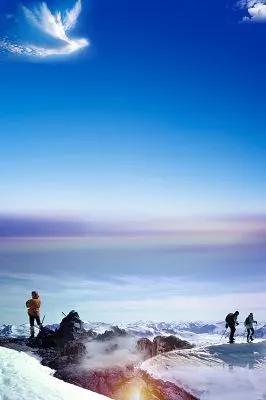
艺术是异化世界中的异化存在。
在训练营电影中,青少年正是通过这些。
异化!

的艺术表达和行为,构建起对抗规训的私人领地。
他们的反叛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被压抑主体性的觉醒与伸张?
训练营教官的角色常呈现惊人的复杂性,他们既是规训的执行者,又往往成为转变的催化剂!

《死亡诗社》中的基廷老师、《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马修老师,都以非传统教育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的教学方法本身就是对体制的温和反叛。
这种角色设置暗示了一个深刻洞见:真正的教育不应是单向度的规训,而应是双向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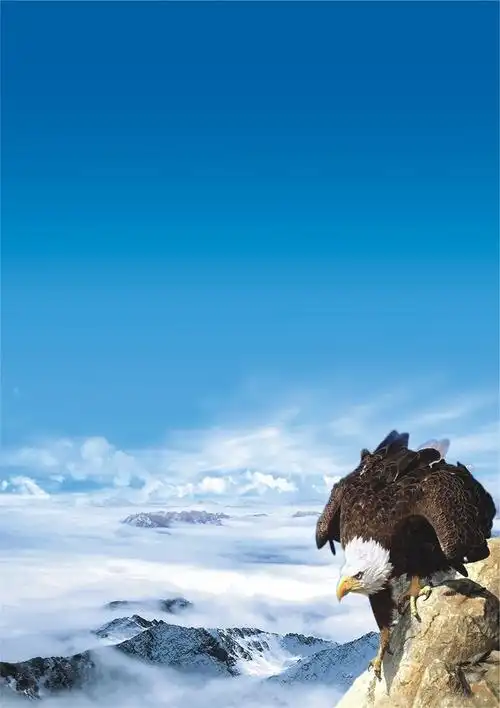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教育论》中写道:。

教育只有在它是自由的时候才是教育。
训练营电影中的开明教育者形象,正是对这种自由教育理念的影像诠释!
青少年训练营电影的结局往往意味深长;
《死亡诗社》中以安德森站上课桌高呼;
船长,我的船长?
作结,《放牛班的春天》则以学生们飞出窗口的纸飞机告别恩师;
这些场景超越了简单的反抗胜利,展现出规训与反叛之间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告诉我们,青少年需要通过与环境(包括规则与权威)的互动来建构自己的认知世界。
训练营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将反叛浪漫化为终极解决方案,而是展示出反叛如何成为成长的必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最终达成某种和解?
青少年训练营电影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权力、反抗与成长的复杂光谱!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规训机构如何试图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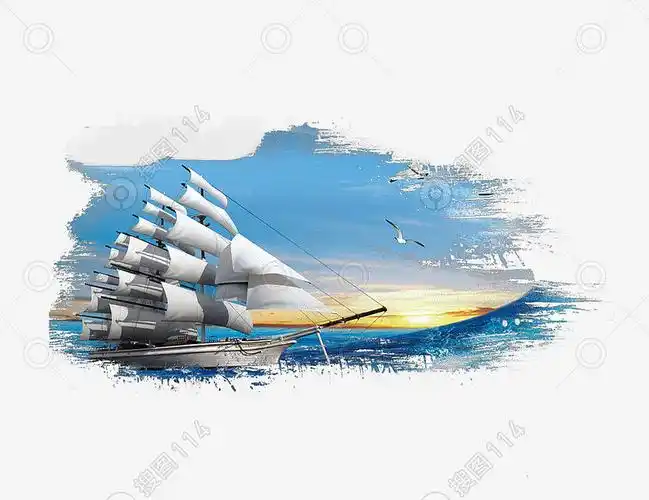
合格。

的社会成员,也看到青春的反叛力量如何打破这种单方面的塑造。
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不应是压制,而是引导?
不应是征服,而是解放;
在规训与反叛的永恒辩证中,或许正如《死亡诗社》所暗示的——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服从,而是教会学生寻找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暂时显得叛逆而不合时宜!